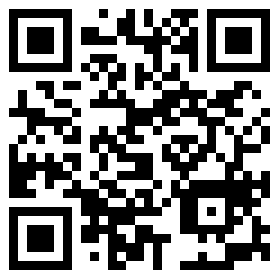坚守,为梦想续航
我校生命科学学院保护生态学研究团队背后的故事
水自竹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上天绝不会辜负那些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依然坚守梦想的人。近日,在四川省大熊猫生态与文化建设促进会2016年年会上,我校生命科学学院作为会员单位获得嘉奖。
2016年,我校生命科学学院保护生态学研究团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团队成员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2项)等项目10余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并获国家林业局竹资源培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熊猫主食竹保育示范基地授牌。团队成员研究成果先后在Scientific Reports、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其中,关于野生大熊猫种群续存最小需求栖息地面积的研究成果在Nature出版集团旗下Scientific reports杂志在线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让我们随着新闻中心的记者,走近这支优秀团队,聆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结缘国宝,逐梦前行
提到中国独有,人们会想到大熊猫;提到大熊猫的分布,人们会想到四川;提到四川对大熊猫的研究,人们会想到亚洲365bet日博。这是一条自然而然的联想链。
我校大熊猫研究闻名海内外,拥有大批“熊猫学者”:国际公认的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奠基人、有“我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把交椅”“熊猫之父”之称的胡锦矗,研究大熊猫栖息地竹子与森林的权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秦自生,中国兽类学会理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委员、IUCN熊类专家组成员张泽钧,WWF王朗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监测示范项目顾问、大熊猫保护生物学家杨志松等。生科院院长张泽钧谈及此事时笑着说:“这是我校与大熊猫长期以来的缘分。”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校以胡锦矗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就开始了大熊猫研究,并且从未间断。人们很好奇,是什么使得这个学校四十年来关于大熊猫的科研成果一项接一项,并培养出一大批活跃在大熊猫研究界的知名学者?
对于生科院的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那么显而易见——传承。例如保护生态学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张泽钧老师自24岁就师从胡锦矗先生。胡老与大熊猫打了半辈子交道,他对大熊猫的真挚热爱,深深感染着张泽钧等后来的熊猫学者。做学问,除了兴趣,更讲心性。这支年轻的科研队伍始终谨记着胡老等前辈的教诲——搞科研要严谨,也要沉得住气。就是这样的精神在这些专家学者与后起之秀间代代相传,薪火相继,延续着那份对大熊猫研究的热爱与责任。在今天,我校保护生态学研究团队不断壮大,从大熊猫及其主食竹研究逐渐拓展到川金丝猴、小熊猫、水青树等同域分布的珍稀濒危物种,并换来了累累硕果。
除了科学研究,这些科研工作者更以保护它们为己任。“现在团队还针对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进行保护研究,了解西南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并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贸易等开展研究工作,”张泽钧自信地告诉记者:“我们的梦想可是很远大的。”
团结协作,续写荣耀
“我们团队一直秉承着开放合作、改革创新、特色鲜明、争创一流的发展理念。”张泽钧字字铿锵,眼中闪着坚定的目光。在他的带领下,我校保护生态学研究团队以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紧密围绕我校建设一流学科的战略需求,团结协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量工作。
为了让这支优秀的队伍更加强大,团队自去年下半年先后引进了周昭敏、彭西、韦伟和韩菡博士。来校后,周昭敏和韦伟在今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韦伟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资助。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潜心于研究是一种使命,而在培养学生方面花费大量的精力,则是一种担当。论文《实测研究:大熊猫最小栖息地要求》的通讯作者杨志松副教授主要从事圈养大熊猫野化放归与小种群复壮研究。他提到,在做科研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一直是这个团队的传统。“研究生刚进校,我就会引导他们初步确定研究方向,然后督促他们大量地阅读文献,积累基础知识。甚至有一些同学在本科时就开始跟着我进行一些研究性的学习。”
“在教导学生这个方面,本科生科研能力较弱,当然花的精力更多。刚开始,肯定没有很多经验,但经过学习之后能力就会有所提升。例如青菁,在做自己第二篇文章时明显比之前更有经验,学会了独立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杨老师提到爱徒青菁时也是一脸自豪。
“时刻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只有学会合作,加强团结,才能更好地体现自身价值。创新更是科学的源头,做科研要保持鲜明特色,才能体现自身价值。”团队成员、我校生命科学学院2013级硕士青菁一直谨记着导师的教诲。
“学院的学术氛围很浓,经常请专家来交流、组织学术沙龙。导师要求我们广泛阅读文献,鼓励我们参加学术会议,争取机会让我们做学术报告。”张泽钧的研究生,现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读博的曹丹丹和在重庆大学读博的洪明生都在全国性会议上做过学术报告。
科研工作者安然于学术研究,专注于撰书立著,好像是件无可厚非的事。对此,张泽钧则有不同见解。“我们鼓励团队多开展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他饶有兴趣地讲起2012年受国家林业局邀请去甘孜州稻城评估一个改善藏区交通状况项目的情形。当时的318国道路况非常差,加之遭遇暴风雪袭击,从康定到稻城走了将近两天。他讲到,在2016年再次应国家林业局邀请去稻城参加一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时,318国道沿途修建得焕然一新,原来那种颠簸折腾、车子开过去尘烟滚滚的境况再也没有了。“通过参与这样的项目,能够把自己掌握的知识运用在社会服务上,当时觉得心里非常高兴。”
因协作让研究成果变得更为丰厚,因团结让队伍变得更有能力去奉献。“在另一种层面上,开展具体的社会服务,也扩大了我们学校对外的影响。我们需要走出去,把学校牌子打出去,做一支有‘担当’的科研团队。”该团队建设亮眼的特色之一就是强调社会服务,包括每年承担多项横向合作科学项目。例如,与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站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培训各个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参与华蓥山自然保护区的创建,草坡自然保护区、白河自然保护区的升级,等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当有人埋怨时间过得太快时,总有人在与时间赛跑。做科研更需要坚持,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时值严冬,当很多人还在温暖的被窝中酣眠时,研究团队成员就踏上了去实验室的小径。一进实验室就立马进入状态开始做研究,分析数据、整理样本与材料……有时当研究进行到关键时刻,或者是有一个节点卡住时,熬夜到一两点是常事。
主要负责室内工作和数据分析的青菁提到,要对非常庞大的数据进行精确计算本来就不易,但工作了一两天后,发现有错或是数据有偏差,又需要重头开始计算,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在研究过程中时不时会遇到问题,大家往往都有自己的看法,为此争论得热火朝天,错过了饭点也不感觉饿。”青菁回忆起这些事情,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唇角带着笑。
“我们做大熊猫研究不可能整天待在实验室里,有很大一部分工作需要实地进行样本资料的采集。”在深山密林中跋涉,在常人眼中可能是怎样浪漫的一幅画面,可实际呢?在野外考察时,队员们常常背着帐篷、睡袋、科考设备还有锅碗瓢盆和大米,早上8点不到就要上山。因为走的都是“兽径”,路途艰辛,充满危险,在野外常常靠吃干粮果腹,往往到晚上8、9点才下山。夏天的蚊虫叮咬都是小事,最难熬的是冬天山中刺骨的寒冷。如果无法下山,就只能生一堆火,围在边上蹲一夜。
“出野外收集数据,十几天不洗澡、不换衣服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杨志松开玩笑说到:“有时候刚从山上下来,很多人见到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在山上架线、修路的民工呢。”
在无数野外任务中最让杨志松记忆深刻的是那次去冕宁开展的大熊猫调查。晚上调查队在山上下不来,只得暂时住在山上的电站里。有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半夜真下起了暴雨。带队组长严文龙很有经验,提醒大家要警惕,他自己则一直在守夜。果然不出所料,深夜大家突然闻到了一股很大的泥腥味,睁眼一看,被眼前骇人的场面惊呆了——泥石流顺着河沟汹涌而来。幸好大家提前有所防备,及时撤离了电站,没有造成伤亡。当撤到安全地方回头再看时,刚才落脚的地方已经完全被泥石流摧毁。回忆起这件事,杨志松拍拍胸口还觉得有些后怕。“真没想到会有这么意外的情况发生,谢天谢地大家都安全回来了。”
为了揭示野生大熊猫种群长期生存所需要的最小栖息地面积,张泽钧、杨志松、青菁等前后花了五年时间,包括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谈起其中各种苦楚,很多人显得云淡风轻。而所有的汗水终于浇灌出了成功的果实。利用大熊猫分布位点(包括粪便和觅食痕迹)数据,他们最终计算出了野生大熊猫种群长期生存所需要的最小栖息地面积——114.7平方千米。“这意味着小于这个面积的大熊猫种群难以长期存活。”我校保护生态学研究团队的这一发现对野生大熊猫小种群的科学保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辛苦和枯燥的科研工作,是这支年轻团队不变的坚守。从开始与国宝大熊猫结缘至今,他们一直坚守着自我与梦想。从团队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无论梦想有遥远,只要心如磐石,步履坚定,星星会说话,石头会开花,在穿过夏天的木栅栏和冬天的风雪后,我们终究会抵达。

张泽钧老师在大相岭保护区

杨志松老师在野外考察